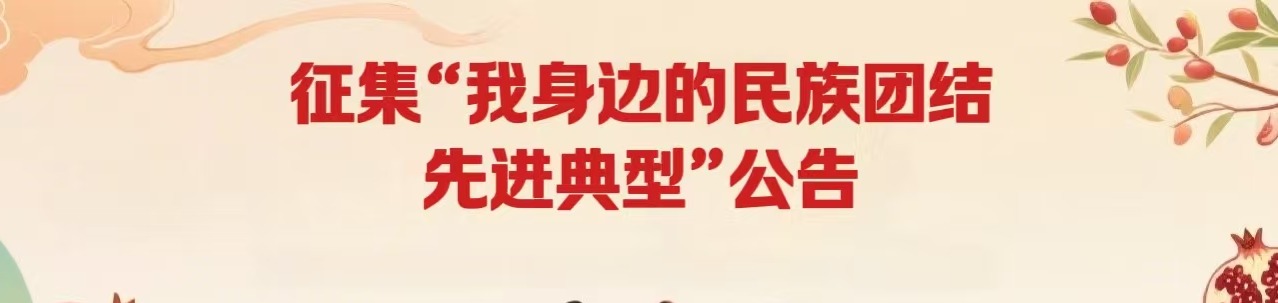父亲和我的新疆缘
骆治纬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地理上被归为“南疆五地州”。她留给我的印象,是版图上茫茫浩瀚的面积,足足47.15万平方公里,仅一个若羌县就有20.23万平方公里、面积接近我的故乡江苏省两倍。当然,大名鼎鼎的库尔勒香梨,也产自巴州库尔勒市,是新疆唯一连续多年入围全国百强县市的县级市。
至今,我都还未能有幸到过巴州。但是,巴州却如“旧相识”,在我的记忆里仿佛存在了千年。读过历史的都应该知道,楼兰故城就在巴州,壮烈的土尔扈特部东归有一部分牧民就安居在巴州,当然还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塔里木河。这些恢弘的历史、自然奇迹,交相辉映在巴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是多么荣光啊!
其实,让我对巴州魂牵梦绕的,还因一个名叫“轮台”的地方。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父亲跟随单位于2006年来到轮台县工作,那时我正好读大学三年级。从那一刻起,我感觉和这片土地就滋生了长久的情感共鸣,也听到了许多有关新疆的真切感悟。

少年时候的我,十分调皮且好吃,父亲摸准了我的性格,一年一度从新疆返乡探亲时,他的行李箱里除了几件衣服,便是满满的新疆干果、水果。春节看到父亲归来的瞬间,我喊了一声“爸”,立即去翻开他的行李箱,看看有什么礼物、有什么好吃的——香梨、葡萄干、核桃、杏干……其实,父亲接到单位通知去新疆工作的时候,祖母、母亲是万般不舍的,我倒是一脸兴奋,缠着父亲,让他给我讲讲新疆的故事。父亲总是和我说,新疆地广人稀,老乡们很淳朴,沙漠里冬季也会下很厚的雪,动辄半个月出不了工作的基地,抬头看着月光,低头思念故乡。
2006年,手机还不怎么普及,家里只有座机。我在东北沈阳读书,祖母和母亲在江苏老家,一家人三个地方,只能互相默默祝好。不过,家人约好,每个星期通一次电话。学校宿舍楼下有一间供学生集中打电话的屋子,往往要排着队等待通话。电话的那一头,父亲给我讲述着石油工人的点点滴滴,虽不能亲至,也很能感受到那份艰辛。有一次父亲发来一份材料让我修改,题目是《沙场秋点兵——XX单位组织大比武》。那些激情飞扬的词句里,我感受到父亲和他同事们朴素的奋斗精神,誓言要打出塔克拉玛干沙漠里一口口油井。父亲是十分普通的工人,任劳任怨为了家人、为了工作,也为了荣誉感。有一段时间,父亲没打来电话,我那时也没有当回事。过了很久,与父亲同去的叶叔叔辗转联系到我,告诉了我缘由。因为一次油井事故,队里决定安排技术员先行下井探勘,按照约定俗成,有成年儿子的人要先下井。父亲没有犹豫,带头和叶叔叔下了矿井,用很长时间处理了那次突发事件,所以没有联系我们。当我听到这段描述时,一时间不知如何表达,仿佛父亲对我而言是失而复得的。让我尤为难忘的是2009年夏天,全家人守在电话机前,焦虑万分地等着父亲报平安,一天、两天、许多天,父亲终于姗姗来迟地告知“一切安好”。我记得,祖母只说了一句话“早点回家”。那年冬季,我们见到了父亲,仿佛这一整年是如此的漫长。2010年,父亲转岗回到了故乡,来到离我工作乡镇不远的矿厂,仿佛过往岁月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他对一切都安之若素。

许多年后,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也来到了新疆,作为援疆干部,生活在伊犁河谷。临别时,祖母早已仙逝,父母妻儿送我到单位门口,我能感觉到他们的万般不舍。但是父亲坚定的眼神却告诉我:到边疆工作是人生历练,莫要辜负。如今,入疆工作已经是第三个年头,我也早已从起初的“单纯向往”过渡到“冷静思索”。援疆三问“来疆为什么?在疆干什么?离疆留什么”时常萦绕在我的心间。我走过了伊犁的每个县,从城市到乡村、部队,我看到了、听到了许多因为各种原因驻守边疆的人物和故事,也试着用笔墨小心翼翼描绘伊犁、描摹新疆,让我和这片土地产生长久的共鸣、累积深厚的情愫。
独特的地缘环境、深厚的文化积淀、丰饶的矿产资源、瑰丽的自然环境,让伊犁在世人心中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印象。来到伊犁工作,我感到莫大荣幸。父亲鼓励我,说我现在所处的岗位、面临的环境都十分优渥,我应该十分珍惜。他也时常对我说,他当年来新疆是工人,而我现在是援疆干部,肩上的责任更重,切莫辜负这一切。在许许多多的日夜里,当我困惑、焦虑时,总会想起父亲说的话,想起他在巴州时已不年轻却依然激情燃烧的岁月,内心深处充满敬意,也给了我希望。
我时常想,援疆结束前,我一定要去一次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看看他眼中瑰丽的南疆。其实,无论北疆南疆,她对我都如艾青先生所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