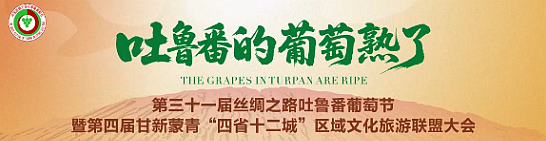大青山的自由精灵
终于在7月最丰盈的季节,我再次踏入大青山。自2021年9月那群野性的精灵——普氏野马被放归于此,这已是我第七次踏上探望它们的旅程。野马回归40周年与它们落户大青山四周年双喜交织,这份因缘际会,让我有幸借出差之机再度奔赴这片魂牵梦萦的绿海。
今年8月6日,一场由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联袂举办的野马回归40周年盛典开启。此前,新疆林业和草原局宣传信息中心副主任尹素萍带队,汇聚了8人组成的专题采访组,用五六天走访内蒙古大青山、宁夏贺兰山、甘肃敦煌西湖三大国家级保护区。
7月13日,经过3个多小时的航程,呼和浩特的熟悉气息扑面而来。匆匆吃过午餐,在大青山古路板管理站内,我们与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领导及工作人员进行了简短的座谈。而后,车轮卷起尘烟,载着我们奔向心心念念的野马放归地。
抵达目的地已是下午4时。东侧山坡上,8匹野马静立如雕塑,正向着我们的方向凝望。三四百米的距离之外,它们的身影清晰可辨,其中一匹今年新生的幼驹,是准噶尔358号5月15日所产,是一匹小公主。我们一下车,便见两辆越野车已停驻——青橙融媒拍摄大青山纪录片的团队正在此捕捉大青山野马群的身影。还见到了在这里日夜守护野马的刘满元和刘素元兄弟俩。

普氏野马在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张赫凡摄
目光南移,另一幕画面在绿波中铺展:以准噶尔370号公马为首领的9匹野马群,正悠然埋首于茂密的青草间采食。野马野放站负责人王俊恒引我缓步靠近。野马们带着一种熟稔的亲昵,纷纷向我们簇拥而来,一点也不怕人。记者们穿梭于花海和绿浪间,镜头瞬间向这群野性精灵聚焦。我的目光则被牢牢钉在眼前:碧波翻涌的绿海之上,野马群游龙一般在花丛中浮动。那些很多我未曾见过的野花,泼洒出蓝紫金黄的斑斓,在7月的风里摇曳。心潮如沸,我忘情地追逐着野马的身影,镜头贪婪地捕捉每一个瞬间。脚下清溪暗涌,漫过草丛,悄然浸湿鞋子也浑然不觉。青橙融媒的镜头悄然尾随,将我与野马重逢时的激动,也定格成了大青山记忆的一部分。
7月的大青山,是最美的季节,今年春季以来,雨水格外丰沛。经过连场透雨,仿佛沉酣初醒的巨人,通身焕发着逼人的青翠。山野间,新草疯长,淹没了往昔的痕迹,像大地铺开了新裁的绿绸缎,浓烈而柔软。这绿意是如此蓬勃,一直漫向天际,与连绵的远山交融。人立在这无垠的绿海之滨,目光所及,尽是层层叠叠、深浅交织的绿。
循着绿意最深处走去,便有泠泠水声透出。山涧小溪在夏日充沛的雨水中丰腴起来,水流饱满,清澈见底。水边草色更深,草叶俯身探向水面。空气里氤氲着水汽与青草揉碎后的清芬,沁凉湿润。
就在这绿浪翻滚的深处,野马群的出现,宣告着真正主角的登场。普氏野马,如同大青山古老而自由的主人,从草海的某个褶皱里悠然漫步。它们土黄色的皮毛在7月的骄阳下流淌着油亮的光泽,粗壮的脖颈高昂,鬃毛如飞扬的战旗。马蹄踏过饱含水分的丰草与松软的土地,发出沉闷而富有节奏的擂鼓之声。它们成群结队,如一股股强劲的棕色激流,在绿色的海洋里游弋。
它们奔向低洼处的小溪,低头畅饮。清冽的溪水映出它们健硕的倒影,又被踏碎的涟漪揉皱。水流漫过它们的蹄腕,带起细碎的水花。饮罢,领头的公马昂首长嘶,声音穿透绿野,马群便再次启动,汇成一股奔腾的洪流,向更深的草海与山麓奔去。它们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融入了那片起伏的浓绿,成为绿浪里几个跃动的音符,蹄声也渐渐被风声与草浪的合鸣吞没。然而,那野性的生命力已然注入这片山水。
拍完这准噶尔370号的家族群后,我去山上寻找有新生马驹的母马群。走着走着,发现簇簇灼目的红与黄,刺破一片沉酣的绿意——那是山丹花。野马的蹄声有时会踏破这片绚烂的寂静。土黄色的洪流裹挟着草屑与泥土的芬芳,从绿涛中奔涌而来。它们强健的躯体撞开深草,蹄下生风。有时会被深草完全淹没。

普氏野马在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张赫凡摄
在这大青山7月的怀抱里,丰沛的雨水和阳光,共同喂养出这片浓绿。野马是绿浪中跃动的精灵,是这片土地粗犷而自由的灵魂。它们的每一次奔腾,每一次埋首青草的安然,每一次迎向故人的轻嘶,都是对守护者最深情的慰藉。而这片丰美的草场,这无尽的绿,便是大地最慷慨的馈赠。
7月的风饱蘸着水汽,将大青山每一道褶皱都染成浓得化不开的碧色,这是野马回归故土四十周年,亦是它们落户大青山四载的丰饶之夏。雨水慷慨,草浪汹涌,铺展成我记忆中盛大的绿海——丰美得令人心颤。每一次车轮碾过通往放归地的土路,每一次呼吸里充盈青草与泥土蒸腾的气息,都让我涌起长住不去的渴望。然而时间如指间流沙,此行我们仅有两天光阴。当记者们拍完返程时,我则执拗地留了下来,宛若仙境的大青山,奔放不羁的野马群,怎么也拍不够。
心系着那群带着新生马驹的精灵,我独自走向山顶。青草没过膝盖,在晚风里起伏如波。然而山顶空空,唯见苍茫暮色涂抹远山。山下传来刘满元的声音:“快下来,它们下山往北去了!”我们上车,向北走,目光扫过每一片草甸和树林,却始终不见野马的身影。折返途中,心有不甘地再次向西搜寻,在刘满元的帮助下,终于在铁丝网围栏边缘的深草丛中,瞥见了它们警惕的轮廓。与准噶尔370号马群的亲昵不同,这群野马显然保持着更深的野性。我一靠近,尚在300米开外,它们便骤然启动,向着远处那片蓊郁的树林疾驰而去。马在花海中奔腾。暮色四合,西天正燃烧着晚霞,灰蓝的云层被熔金与玫瑰红撕裂,泼洒在苍翠的山峦之上。我按下快门,将这稍纵即逝的绚烂摄入心底。我们约定明晨6时再来拍。

普氏野马在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张赫凡摄
风依旧吹送着,绿浪不息。远处,刘满元的小小身影立于草坡之上,凝望着野马消失的方向。他亦是这绿海中的一粒微尘,一个静默的守望者。当月光开始清洗山野,大青山深处,青草正温柔地裹着那些自由的马蹄印。一年间,他们兄弟俩至少360天都守在这里,与野马相伴相依。他们守护的不仅是一个物种的存续,更是在这喧嚣时代,为一种古老而高贵的自由,保留了一片无垠的疆域。
回到酒店已是晚上10时多。第二天凌晨3时30分,越野车载着我们一头扎入大青山的怀抱。凌晨的山顶,凛冽的风如冰冷的刀锋,轻易刺透单薄的T恤和防晒衣。天色青灰,东方天际线处,只吝啬地裂开一道橘红与金黄的细缝,旋即被厚重无边的灰云吞没。期待的日出落空了。5时30分,带着一身寒气,我们转向野马放归的核心之地——什字沟。
大约6时整,抵达刘满元兄弟守护山野的简陋居所。一碗热茶就着香酥饼下肚,暖意稍回。车行三四公里,晨光熹微中,放归地的草甸如一块巨大的、饱含露水的绿丝绒毯铺展眼前。两群野马,隔着一道低缓山脊上的铁丝网,正沐浴在破晓的清辉中,安详地休憩、交流,轮廓在薄雾里晕染出宁静的剪影。
我端起相机,踏进密草深处的小径,这是野马踏出的马道。草尖上沉甸甸的露珠瞬间浸透了鞋袜和裤脚,冰凉地贴着皮肤。我竟得以悄然靠近那带着幼驹的马群,最近时不过10米之遥。镜头贪婪地捕捉:小马驹依偎在母亲腹侧的甜蜜,成年马匹肌肉在晨光下流畅的线条,它们偶尔甩动头颅时鬃毛划破空气的瞬间。直到青橙融媒的拍摄队伍靠近,马群才警觉地缓缓向更开阔处移动。隔着围网,马群里那标志性的沉稳首领准噶尔370号清晰可见。更远处,一只狍子被惊起,灵巧的身影在山坡上一闪即逝。整个上午,我的脚步便在这两个马群之间穿梭不息——上山,下山,追逐,守候。山势起伏,常在不经意间出现一片平缓台地,马群便驻足其上,安详地休憩。
准噶尔372号快要生产了,腹部浑圆。我凝望它缓慢移动的轮廓,目光里盛满温柔的焦灼——这匹母马已在绿海中静候近月,腹中新生命的悸动牵动着每一颗守望的心。大青山今夏第一个幼驹的蹄音犹在耳畔,我们多么渴望此行能见证第二个新生命破晓般的初鸣。
在苍翠油松的掩映下,准噶尔370号正上演着截然不同的激情剧。这位马群的首领,似乎被7月丰沛的生机撩拨得心神不宁。它时而隔着铁丝网,向对面马群中的母马发出低沉而殷勤的嘶鸣,脖颈伸长,鼻翼翕动。时而又转向自己群内的伴侣——准噶尔359号,温存地靠近,试图以鼻尖轻触,以身躯依偎。然而,回应它的常常是母马毫不留情的拒绝。准噶尔359号或是猛然扬起后蹄,或是干脆在关键时刻灵巧地扭身避开。这求而不得的躁动,与准噶尔372号腹中沉静的等待,在7月的草甸上交织成一首野性而真实的生命二重奏。

普氏野马在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张赫凡摄
丰沛的水草滋养了生命,也催生了恼人的蚊蝇。它们乌云般盘旋,死死纠缠着野马的眼睛、口鼻和脊背。马匹们不堪其扰,尾巴急促地甩动如鞭,头颅猛烈地上下点顿。当正午的骄阳升到顶点,终于完成预定拍摄下山时,汗水早已浸透T恤。站在稀疏的树荫下,山风陡然强劲起来,带着草叶的清冽。仰头灌下一瓶冰凉的矿泉水,那透骨的凉意直抵肺腑。
11时30分,采访组的记者开始对王俊恒进行采访。他讲述着野马回归的艰辛历程、大青山生态恢复的喜人成果,言语间满是守护者的自豪与深情。采访尾声,需要拍摄他与野马互动的画面。记者们随他登上半山腰,镜头对准了他凝望远方的坚毅侧影和山下悠然移动的马群身影。
就在我们准备撤离时,那带着马驹的群体竟从山坡上奔腾而下,径直冲向一片开满白色野花的洼地。花朵洁白如雪,植株跟人一般高,马群闯入其中,瞬间被淹没又浮现。它们继续向北,最终隐没在更为浓密的深草丛中。时间紧迫,我几乎是屏住呼吸,猫着腰悄悄潜行靠近,抓住这最后的宝贵时机,让快门声在寂静的草海里密集响起。直到远处传来催促的呼喊,我才恋恋不舍地转身,向等待的车队跑去。

普氏野马在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张赫凡摄
下午,转往大青山管理局,科研监测处的张俊华处长细致地为我们梳理了保护区多年的科研监测情况与野马种群动态。野马已从最初的12匹增至17匹,其中繁殖成活马驹8匹,普氏野马在内蒙古野外繁殖成功,进一步丰富了大青山的生物多样性,成功实现其在内蒙古高原南缘的华北区与蒙新区过渡带种群扩散与扩大放归。骄人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守望与心血。
他说,由于野马争雄打斗及疾病原因,已损失3匹公马,现只剩一匹公马准噶尔370号,他们已给新疆林业和草原局发函,准备引进3匹公马,争取今年9月将马运过来。
13时多,飞机载着我们腾空而起,飞向此行下一站——银川。舷窗外,大青山的轮廓在云层下渐渐模糊、淡去,最终化作地平线上一抹温柔的青痕。然而我知道,那片丰茂的草海,那群奔腾的精灵,那灼灼燃烧的山丹花,以及那浸透了露水与汗水的每一个瞬间,已如烙印般刻入心底。这丰饶的7月,这短暂的两日,我把心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那片绿浪翻涌、马蹄声碎的自由之地。(作者:张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