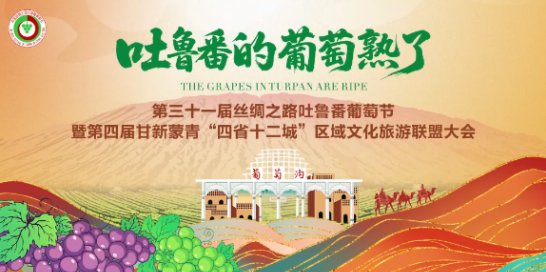石榴画评丨水墨的荒野——观韩子勇西域水墨作品展
沈苇
韩子勇是我的西域兄长,具有批评家、学者、诗人等多种身份,在他身上呈现了博识、睿智、开阔视野等综合素养。这批作品,名之“西域水墨”,也是当代文人画,更准确地说,是现代主义文人画,呈现的是现代意识观照下的亚洲腹地自然地理和精神地理,而非风情化、风景化了的新疆。

7月26日,“行走 观想 表达——韩子勇西域水墨作品展艺术沙龙”,在新疆油画学会学术交流中心举办(资料图)。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马晋轩摄
子勇兄是思想者,水墨和笔触中有哲思,蕴含着一个宏阔的文化背景,在重构新疆的“地景哲学”;他是诗人,以文学为骨骼、水墨为肉身,拓展新疆的审美空间和诗学空间。在精神传统上,是向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人画源头致敬,并与我的湖州老乡赵孟頫“诗画同源”的主张相呼应。简言之,这是文学性的绘画,是“思与诗的水墨”。
子勇兄主要画的是荒凉事物:旷野、戈壁、废墟、小路、远山、胡杨、红柳、沙尘暴等,大多集中于“荒野主题”,当然还有绿洲白杨,“白杨如炬”那种热烈,“西域白杨似情眉”那种深情和柔情。他出生于准噶尔盆地边缘的兵团农场,荒野是天赐的无边风景,他曾告诉我上大学才看到柏油路,像黑色绸带飘在大地上,从小到大看到的和走的都是土路、荒野中的路。有他的诗为证:“上车吧/就这样走上七天七夜/哪怕天天是一模一样的戈壁滩/没有人能开除我的生活/哪怕一年也遇不到一个村庄。”(《没有人能开除我的生活》)

展览中韩子勇(右)、刘宾(中)、沈苇(左),围绕新疆文艺创作展开讨论(资料图)。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马晋轩摄
这些作品首先唤醒和表达的是个人记忆,是一个人的纸上还乡、精神还乡。2012年他离疆进京时写过这样的诗:“现在我就要走了/带着洗不掉的大戈壁气息/带着石头铺出来的记忆/我到哪里/都只能带着你们的模样/我到哪里/灵魂都会悄悄回到原处。”(《我这块石头》)这些画作就是艺术回归故乡、灵魂回到原处。但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他画出了一个意义的荒野、启示的荒野,画出了荒野的主体性。勿以为我们人类是唯一主体,荒野也有一种天然的主体性,与人类的主体性互为镜鉴。在新疆题材绘画中,绿洲、草原已画得很多,风情已经泛滥,画荒野却十分少见。生活在新疆,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荒野。我回归故乡已六年多,新疆仍是我心目中神圣的存在,是我的天涯咫尺、不在场的在场。沙漠是大荒、绝域,却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录式的背景。
欣赏这些出色画作,凝视水墨的荒野,我想起梭罗《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荒野中蕴含着这个世界的救赎。”子勇兄曾说:“中国文学需要边疆精神的鼓舞”,今天,我想稍稍改动一下这句话:文化不可缺失荒野精神。世界的救赎在荒野,世界的启示在荒野,世界的开端和结束在荒野……荒野是荒凉中的丰饶、冷寂中的炽热,真正代表了新疆表面上的荒凉和骨子里的灿烂。即使画作中大量的留白,也不是空无和虚无,而是以虚写实,于无声处的惊雷,赋予并呈现了一种终极关怀和启示。
除了“去风情化”的特点,子勇兄的西域水墨在地域性表达中“去地域化”,宣告了边疆经验的主体性回归,与此同时,还具有人类学和生态学意义。人类学强调具备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以及“理解之上的理解”,子勇兄的绘画不是他者视角、旁观者的一瞥,而恰恰来自文化持有者的内部、深处,以及对新疆的无限热爱和理解。就生态学意义来说,他是用自然生态来反观精神生态,反观人类的绝望和希望、困境和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