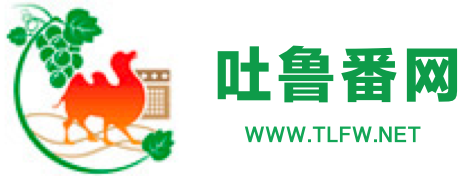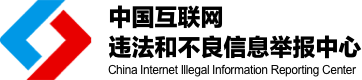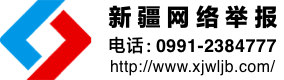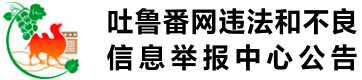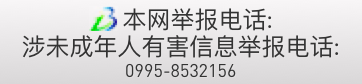人世沧桑,唯有时间
黄昏时,我在微信对话框里,突然就打出了“人世沧桑,唯有时间”几个字。这好像有点不通,但它似乎提醒我不要修改。
接收这句话的老友,前不久痛失了相识相伴32年的夫君。
我木讷地劝慰着她保重,但同为中年人的我们都知道,保重之法是稀缺的。最后,谁都是靠着时间的搀扶走过了痛苦的日子。
她感叹:今天刚刚送走了集团里的一个才子,也是1968年的。
一个月前,大雪后奇寒的一天,我在一个叫九里山的公墓里,找到了我的老班长也是我师父的墓碑。他生于1969年。
那天最低温度接近零下20度,我给他的墓清扫了积雪,用快要冻僵了的手给他擦拭了墓碑,打开一瓶二锅头,心里和他说着话。
我转了几趟地铁,又打的和步行,才来到九里山。网约车在陵园门口停下后,我给司机发了一个小红包。
那天大雪覆盖,晴空万里,四望无人。我正担心找不到他的墓,突闻两个墓园清洁工大爷的对话,一抬眼,老班长的墓就在那里。
老班长知道我笨,就连我来看他,都有“向导”。
千里之外,在南京的彬彬让我把此时此刻“直播”给他看,这可能是世上最悲凉的“直播”。
我和彬彬是他共同的兄弟和“徒弟”。
开着手机视频,我想起有一次他来南京出差时,他难得没被饭局给“拖”走,而是深夜时分在宾馆房间和我静静地喝着小酒。中间他发了条朋友圈,然后得意地让我看着上百个“人头”瞬间在点赞和评论区浮现、跳动的场景。我的微信上,有一千多名微友,但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头”为我跳动。
第二年,他住院开刀了。
三年后再住进北京一家医院时,他依然能把护士站的护士逗得前仰后合,却在回到病房后对我说,“背疼,帮我按一下。”
他删掉了几千个微信好友,只留下几个。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洞察了人性和生命。他的微信上再也没有几百个“人头”集体为他跳动的场面,但我对他说,他的文字变得洗练而有深度了。年轻时,我总嫌弃他文采不够好。
那年三月,他来南京,约了我在夫子庙小聚。我说,医生不让你喝酒。他说,“去他的不让喝酒。”于是我们浅浅喝了一顿酒。
我们说了漫长的话,他像是在郑重地和我告别。
那年四月,他回到北京后就各处求医,极力延迟死亡的到来。情势已经万分危急,他却还记挂着我父亲的开颅手术,几次把我父亲的片子传给名医看。我不忍心,他说:“我是你哥。”
那年七月,我永远地失去了我师父、我哥,一个暴烈性和幽默感总能毫不违和地安装于一身的人。
去九里山的途中,在一路向北的地铁上,我看到了一群穿着羽绒服的半大孩子,在冰天雪地的操场上踢球。他们拼抢着、欢呼着。他们长大了,也会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吧?
我想起32年前第一次见到老班长时,也是和一群十八九岁的同龄人在洛阳龙门石窟附近的冰天雪地里踢正步,在休息时间里为着莫名其妙的乐子欢呼。
那年冬天奇寒,零下十几度,我喜欢的南京作家程玮在散文里的第一句:南京奇寒的那天。那篇散文发在扬子晚报上,报纸是文友从南京寄到新兵连的。
那天,我师父大声喊着我:“刘万志,来一下!”
他是作为团部报道组的代表来“考察”我的。我下连下到几百公里之外的大山里后,有一次他到山里采访,顺便到四连瞄了我一眼。见面时,我刚从坑道里扒渣回来,脸上厚厚的灰,军装都快看不清颜色了。我站得笔直,对他恭恭敬敬地说,“感谢班长的栽培。”他看着我傻乎乎的样子直乐,然后对连长说,“这就是刘万志。”
虽然我的名字被他凭空喊少了一点,但我从此进入了他的“朋友圈”,直到把他所有的时间都给耗尽。